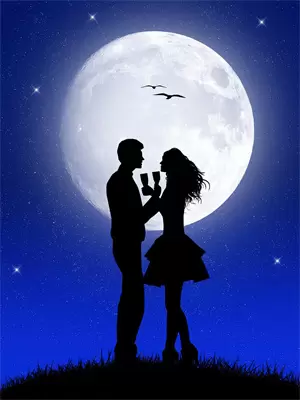女孩自我救赎和账户救赎的故事第一章 山野童年我的世界,在1988年那个夏天之前,
是完整而明亮的,像望天畈八月湛蓝如洗的天空。我叫林晓静,
1981年生于赣鄂交界处一个藏在群山褶皱里的小山村。这里的天总是很蓝,云走得慢,
时光也仿佛比山外流淌得缓。春天的信号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我们叫它映山红,红得灼眼。
我们这群野孩子会钻进花丛,小心翼翼地掐下花朵,拔掉花蕊,
吮吸底部那一点点微乎其微的甜意。夏天是狂欢节,村口的池塘是我们的乐园,
一个个晒得像泥鳅,扑通扑通跳下去,扑腾起混浊的水花,惊得青蛙四处逃窜。午后,
举着长长的竹竿,顶端粘上用面粉揉成的面筋,去粘那些在树梢声嘶力竭鼓噪的知了。秋天,
稻田变成了无边的金色海洋,风过处,沉甸甸的稻穗摇曳,沙沙作响。我们在田埂上疯跑,
追逐着红蜻蜓,偶尔会偷偷扒开别人家田里的泥土,挖出几个细长的红薯,捡来枯枝败叶,
点燃一堆小小的篝火,把红薯埋进火堆里,烤得外皮焦黑,掰开来,却是金黄喷香,
烫得我们龇牙咧嘴也舍不得放下。冬天,山风像小刀子一样凛冽,
我们挤在谁家温暖的灶膛前,听着柴火噼啪作响,分享一把炒豆子或是烤得硬邦邦的年糕片,
央求围着蓝布头巾的老人讲那些听了无数遍的、关于山精野怪的老故事。家的味道,
是黄昏时分妈妈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搓洗衣物时,身上传来的那股淡淡的皂角清香。
爸爸的肩头,是我童年至高无上的瞭望台。他从田里回来,顾不上擦一把额头的汗水,
就会哈哈大笑着把我高高举起,放在他宽厚结实的肩膀上。坐在上面,
我能看见自家屋顶袅袅升起的、笔直的炊烟,能看见远处蜿蜒如带、通向山外的小路,
仿佛能一直看到天边,看到爸爸妈妈口中那个神秘而精彩的世界。那时觉得,爸爸的肩膀,
就是全世界最安全、最温暖、最高的地方。夜晚,星空低垂,仿佛一伸手就能摘到星星,
蛙声虫鸣汇成一片,家的温暖像一层厚厚的茧,足以抵御世间一切风寒。
第二章 裂缝初现变化的开端,像一场无声的雪崩,始于1988年那个秋天,
父母提着鼓鼓囊囊的行李卷,登上了那辆喷着浓烟、通往南方的绿皮火车。“静静,
在家要听奶奶话,好好读书……”妈妈的红眼圈像两颗烂桃子,她把我搂在怀里,
力气大得几乎让我窒息,那皂角的清香被一股浓重的离别愁绪掩盖。
爸爸只是用力揉了揉我的头发,他的手掌依然宽大温暖,但我却莫名地感到一丝陌生的粗糙。
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村口那条尘土飞扬的小路尽头,也仿佛从此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我被留给了奶奶。奶奶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摩挲着我的脸时,带着一种刺刺拉拉的感觉。
她总是一边在灶台边忙碌,一边絮絮叨叨:“丫头片子,读那么多书有啥用?
养大了也是别人家的人,不如早点学着做家务……”她的眼神浑浊,
带着一种我那时无法完全理解、却本能感到不舒服的、根深蒂固的轻视。但比这更冷的,
是父亲次年春节归来时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一身泥土气息、笑容憨厚的农民。
他穿着笔挺的、带着明显折痕的“假领子”西装,脚下踩着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的皮鞋,
头发梳得油光水滑。他显得阔气而陌生,会带我们去镇上唯一的国营饭店吃饭,
点满一桌子油汪汪的菜,仿佛要用这种方式证明他在外面的成功。然而,有一次,
我亲眼看见,妈妈偷偷塞给来走亲戚、衣衫褴褛的外婆几张皱巴巴的零钱,
爸爸的脸瞬间就拉了下来,像蒙上了一层寒霜。他猛地冲过去,一把将钱夺了回来,
声音像炸雷一样在狭小的堂屋里响起:“我累死累活挣的钱,
不是让你去填娘家那个无底洞的!”外婆窘迫地站在那里,
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无助地搓着打了补丁的衣角,嘴唇嗫嚅着,最终什么也没说。
妈妈像一株被狂风骤雨袭击的、迅速萎顿下去的草,脸色煞白,嘴唇翕动了几下,
最终只是深深地、绝望地低下了头。那一刻,屋里之前那点虚假的热闹和温情被撕得粉碎,
空气凝固得像冰。我躲在门后,看着爸爸因为愤怒而扭曲的、陌生的脸,
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也跟着“咔嚓”一声,碎裂了。
家里那点由父母共同撑起的暖黄色的光,仿佛随着那声怒吼,“噗”一声,彻底熄灭了。
第三章 漫长黑夜经济的窘迫,很快像冰冷的潮水,漫透了我整个学生时代,
成为第一重实实在在的、令人窒息的黑暗。我们村小只有一到三年级,
几个年级挤在一个由旧祠堂改建的破败教室里上课。黑板是木板刷的黑漆,早已坑坑洼洼。
课本是城里孩子用旧了的,传到我手里时,往往已经卷了边,缺了页,封面模糊不清。
但这都不是最难受的。每个学期开学后不久,总会有那么一天,班主任会拿着一份名单,
站在讲台上,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全班,然后开始点名。“林晓静,学费什么时候交?
”那一刻,全班几十双眼睛,会“唰”地一下,齐刷刷地集中到我身上。那些目光,
有懵懂的好奇,有隐约的同情,但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审视和隔阂,
像夏天叮人的小虫子,密密麻麻地爬满我全身。我恨不得脚下立刻裂开一条缝,
让我能彻底消失。我的脸烧得滚烫,像被架在火上烤,头埋得低低的,
几乎要戳进课桌抽屉里,声音像秋后的蚊子,微弱得连自己都听不清:“……快了,
我爸妈……快寄钱了。”“每次都这么说!下个星期必须交来!”老师不耐烦的语气,
像鞭子一样,带着凌厉的风声抽打在我毫无防备的心上。我成了“那个总是欠费的女生”。
课间,女孩子们三五成群地跳皮筋、丢沙包,银铃般的笑声在操场上空回荡,
却很少有人会主动叫我加入。她们聚在一起,分享从家里带来的炒米糖、盐水花生时,
那香甜的气味飘过来,我只能默默地咽下口水,走到操场的角落,
假装全神贯注地看蚂蚁搬家,或者研究一片奇形怪状的树叶。贫穷,
像一堵无形却坚不可摧的高墙,把我牢牢地隔绝在所有属于孩子的、单纯的欢声笑语外面。
我开始害怕上学,害怕每个清晨,害怕那种被公开处刑般的难堪和孤立无援。然而,
这仅仅是黑暗的表层。更深沉、更粘稠、更令人绝望的黑暗,来自我的班主任,吴德。
吴老师教我们语文,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四十多岁年纪,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
穿着在当时看来很体面的、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口袋里别着一支英雄牌钢笔。在大人眼里,
他是个“有学问”、“负责任”的好老师。起初,他对我也显得格外“关心”和“慈祥”。
“晓静,放学留下来,老师给你辅导辅导功课。”他第一次这么说时,
我心里甚至涌起一股卑微的、受宠若惊的感激。我以为,终于有人看到了我的困境,
愿意拉我这个深陷泥潭的人一把。空荡荡的教室,只剩下我和他。
夕阳的余晖像病人弥留之际的喘息,挣扎着透过破旧的木格窗棂,
在坑洼不平的泥土地面上投下斑驳陆离、扭曲变形的光影。他开始还一本正经地讲着课文,
但渐渐地,那双手就不老实起来。它会“无意地”、先是试探性地搭在我瘦削的肩膀上,
然后,像一条冰冷的、滑腻的蛇,顺着我的脊背,慢慢地往下滑。第一次,
那双潮湿、带着浓重劣质烟草味道的手,粗暴地越过一个孩子所能承受的最终界限时,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变成了一片空白。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
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四肢冰冷僵硬,动弹不得。
世界变成了一个嗡嗡作响的、令人作呕的囚笼。“你是好孩子,”他的呼吸喷在我的耳后,
带着浓重得令人窒息的烟臭味和一种难以形容的猥琐气息,“不想失学吧?乖乖听老师的话,
说出去,你这学就别想上了,你爸妈的脸也要被你丢光了……”“上学”,
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改变或许存在的光明未来的稻草,也是父母对我唯一的、沉重的期望。
恐惧像一只无形却力大无穷的冰冷的手,死死地扼住了我的喉咙,
夺走了我所有的声音和力气。我死死地咬住自己的嘴唇,直到口腔里尝到一丝腥甜的铁锈味,
把即将冲出口的尖叫、呐喊和屈辱的眼泪,一起狠狠地、绝望地咽回肚子里,
沉入那无边的黑暗深渊。从那天起,放学后的教室成了我专属的、循环往复的刑场。
我学会了最可悲的自我保护——把自己的灵魂从正在遭受凌辱的身体里抽离出来,
飘到天花板上,像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看着下面那个小小的、一动不动的、如同玩偶般的躯壳。
我会死死地盯着墙壁上一块正在缓慢剥落的墙皮,研究它蜿蜒曲折的裂纹,
想象它是一幅神秘的地图;或者盯着窗外一只偶然路过的、自由自在的麻雀,
看它如何灵巧地振翅,如何欢快地鸣叫,最终如何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广阔的天空。
我的身体,像一座被紧紧封闭、戒备森严的堡垒,拒绝任何人的靠近和触碰。
我害怕所有成年男性,包括村里那些平日里看起来和蔼可亲的伯伯叔叔。
我开始下意识地含胸驼背,用哥哥穿剩下的、无比宽大的旧衣服,
努力遮掩开始微微发育、却让我感到无比羞耻和厌恶的身体。我恨这具身体,
它引来了那道让我恐惧作呕、如同附骨之疽的目光。
第四章 书页微光在仿佛没有尽头的黑暗里,任何一点微光,都显得弥足珍贵,
足以支撑一个灵魂继续前行。真正的转机,发生在我升入四年级的时候。
吴德不再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当我看到课程表上班主任一栏换成了一个女老师的名字时,
那颗一直悬在喉咙口、担惊受怕、紧缩了近两年的心,才重重地、迟缓地落回了原处。
虽然学费依旧时常拖欠,新班主任也会在课堂上公事公办地催促,但我再也不用在放学后,
被单独留在那间弥漫着粉笔灰和噩梦气息的、令人窒息的教室。仅仅是这一点点的改变,
就足以让我感到一种近乎虚脱的、劫后余生般的庆幸。
我终于从那个黏稠、恶心、无处不在的噩梦中,暂时性地脱离出来。也正是在小学高年级,
我认识了更多的字,探索世界的欲望便不再满足于镇上那家灰尘密布、光线昏暗的旧书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同族的一个堂哥家,那个总是静悄悄的阁楼上,
竟藏着整整两大箱子的书。堂哥家与我们家隔了几户人家,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堂伯,
是村里少有的、被公认为有文化的人,年轻时在外面跑过运输,走南闯北,见识广博,
也极其爱买书、藏书。那些书被随意地放在阁楼的角落里,木箱上蒙着厚厚的灰尘,
结着蛛网,但在我的眼里,却像一座沉睡的、等待着我这个探险者去发现的巨大宝藏。
我鼓起了平生最大的勇气,揣着平时帮堂伯母喂鸡、扫地换来的一点微薄的好感,
怯生生地、结结巴巴地提出想借书看。堂伯倒是很开明,看着我这个瘦小安静的侄女,
挥了挥手,爽快地说:“喜欢看就拿去看,别弄坏、别弄丢就成。”从此,
堂哥家那间光线昏暗、布满灰尘的阁楼,成了我新的、更广阔、更自由的避难所。
这里没有催缴学费的目光,没有令人作呕的触碰,只有书页翻动时发出的沙沙声响,
和文字构建起的、无比宏伟壮丽的世界。我开始像一只不知餍足的书虫,
疯狂地、忘我地啃食那些泛黄、脆弱,却散发着油墨和岁月混合气息的书页。
我最早接触的是金庸、梁羽生、古龙笔下那个刀光剑影、侠骨柔情的武侠世界。在那里,
善恶到头终有报,侠客们仗剑天涯,快意恩仇。我羡慕郭靖的憨厚与坚守,
敬佩乔峰的豪气干云与悲情命运,也为李寻欢的无奈和陆小凤的洒脱不羁而心折神往。
在想象中,我仿佛也拥有了绝世武功,可以斩开身边一切令人不快的束缚、欺侮与不公。
后来,我的阅读范围越来越杂,胃口也越来越大。
《青年文摘》、《读者》里那些短小精悍的文章,
窥见校园和家庭之外更广阔、更复杂的社会图景;《南风窗》里的一些时政讨论和经济分析,
虽然我看得云里雾里,半懂不懂,却模模糊糊地让我感觉到,
山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的大潮正汹涌澎湃。
我也翻出了堂伯珍藏的一些外国小说,
理解了什么是牺牲与成全;《呼啸山庄》里希斯克利夫那种狂野而绝望、毁灭一切的爱与恨,
像一场来自荒原的暴风雨,前所未有地震撼了我年幼而苍白的心灵。再大一些,识字更多了,
我开始向中国古典文学的巍峨殿堂进军。《红楼梦》我前后看了三遍,
才勉强理清里面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财和最终的凄凉结局让我扼腕叹息;《三国演义》里的权谋韬略、运筹帷幄我看得半懂不懂,
却深深记住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西游记》则是我最初、最精彩的奇幻启蒙,
满足了一个孩子对神魔世界的所有想象。甚至《山海经》里那些奇形怪状、能力各异的异兽,
《聊斋志异》里那些有情有义、往往比人类更懂得爱与恩义的鬼狐仙怪,
都让我读得如痴如醉,废寝忘食。这些书,我绝大多数都是囫囵吞枣,
很多深意、背景和文学技巧并不理解。但它们像无数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
在我那片因恐惧和贫瘠而近乎荒芜的心田里,被随意却广泛地撒下。它们默默地告诉我,
世界很大,非常大,人生有很多种活法和可能;它们悄悄地教会我辨别善恶美丑,
在我最灰暗、最无助的时候,用无声的文字为我构筑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在这里,
我是安全的,是自由的,我的精神可以挣脱现实的枷锁,肆意翱翔于九天之上。书籍,
成了我穿越童年那片深沉黑暗时,最忠实、最温暖、最智慧的旅伴,
它们一点点地修复着我被撕裂的内心,
默默地、持续地为我积蓄着面向未来的、微薄却坚定的力量。第五章 孤寂青春进入初中,
再到高中,我离开了村小,来到了镇上的中学。环境变了,但我依然是人群中的一座孤岛。
虽然摆脱了吴德的直接阴影,但贫穷的烙印和长期自我封闭形成的惯性,
让我无法融入新的集体。同学们课间热烈讨论着Beyond乐队、小虎队,
传抄着流行歌曲的歌词,或者兴奋地交流着昨晚看的电视剧情节时,
我通常只是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要么假装看书,要么望着窗外发呆。我的内心世界,
依然更多地与《读者》、《青年文摘》里的故事共鸣,
或者沉浸在《呼啸山庄》那片荒凉原野的爱恨情仇之中。
当女同学们开始偷偷传阅琼瑶、席绢的言情小说,为里面男女主角的爱情或哭或笑时,
我却觉得那些故事遥远得有些不真实,远不如《红楼梦》里的世情百态来得深刻。
我几乎没有朋友,也习惯了没有朋友。我把所有无人打扰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和阅读。我知道,
对于我这样的孩子,读书是唯一看似公平的、可能改变命运的途径。我害怕成为人群的焦点,
害怕任何形式的关注,走路总是低着头,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
唯一能让我感到一丝暖意的,是高中的语文老师,陈老师。
她是一位四十多岁、气质温婉沉静的女性,说话总是轻声细语。
沉默、我作文里那些过于早熟和沉重的思考、以及我偶尔与人对视时一闪而过的惊惶眼神里,
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但她拥有一种极其珍贵的、保护少女脆弱自尊的温柔——她从不多问,
从不试图强行撬开我紧闭的心扉。她只是在我下课独自收拾书包时,走过来,
默默地把几本还带着油墨清香的《读者》或《青年文摘》塞进我的书包。
她会在我那些写满了隐晦的痛苦、迷茫和对命运无声诘问的周记后面,
写下长长的、充满理解和鼓励的评语。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晓静,
文字是穿越黑暗的火把。坚持下去,你的笔,你阅读过的书,
终将能带你走到很远很远、有光的地方。”这些细微的、不动声色的善意,
就像我那片漆黑冰冷的海面上,偶尔亮起的、微弱却坚定的灯塔。它们让我在漫长的孤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