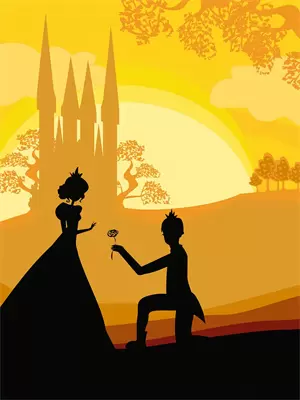我叫盛荣,大盛三百七十年的史书上,
该会郑重记下这个名字——不是以某位帝王的妃嫔、某任太子的姊妹,
而是以大盛开国以来首位女帝的身份。我出生那一刻,整座皇城被天光点燃。
霞光如天河倾泻,万千色彩在云巅翻涌,将九重宫阙映照得宛如神境。
钦天监的老臣伏地而拜,声音颤抖:"天降祥瑞,此乃神女临世之兆!大盛国运,
必将因她而兴!"消息传至边关那日,久攻不下的城池忽然传来捷报——敌军粮仓莫名起火,
主帅坠马而亡。镇北军势如破竹,一路杀至敌国都城,凯旋的军旗染着血色,
却比霞光更耀眼。父皇大悦,在太极殿亲手为我戴上缀满东海明珠的玉冠。"清宴"为号,
"盛荣"为名——他说,我的诞生,便是上苍赐予大盛最珍贵的吉兆。那一年,
朱雀大街的桃花在深冬怒放,西域使节献上的葡萄酒流成了河。人人都说,
小公主盛荣是天道赐给大盛的祥瑞,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传奇。自我记事起,
耳畔便萦绕着"神女"的赞誉。宫人们总说,清宴公主生来便带着祥瑞,冰雪为魂,玉为骨。
父皇每每将我抱在膝头,鎏金龙纹的袖口摩挲着我的脸颊:朕的盛荣,
是大盛最璀璨的明珠。金銮殿的琉璃瓦映着他眼底的骄傲,
让我错觉自己当真能捧住这万里河山的欢欣。母妃因我晋了贵妃位分。可每当夜阑人静,
她替我梳发时,象牙梳总会在某个瞬间突然停滞——铜镜里倒映着她弯弯的眉眼,
可那笑意却像浮在深潭上的薄冰,底下沉着我看不懂的暗涌。
就连最慈爱的皇后娘娘亦是如此,她身上淡淡的沉水香笼罩着我时,
我总能听见她胸腔里一声极轻的叹息。宫墙内共有三位皇子与两位公主。太子哥哥擅画,
四皇兄擅诗,而三皇兄……宫人们从不敢在我面前提起那个早夭的名字。
潇妃所出的大皇姐长我十岁,我五岁那年,她穿着大红嫁衣踏上北国的婚辇。
百官赞她深明大义,我却永远记得那日——她冰凉的指尖抚过我的眉心,
鎏金护甲在雪地里折射出刺目的光:阿荣……余音散在呼啸的北风里。
母妃未显露的泪落在我肩头,像一粒烧红的炭,灼穿了那年隆冬的雪。
我仰头望着渐行渐远的仪仗,学着皇姐的语气呢喃:阿荣……
稚语被朔风卷着撞向朱红宫墙,如同幼雀撞上金丝笼。那时的我尚不明白,
这满宫的笑靥之下,藏着怎样锋利的暗礁。七岁那年,
安将军的幼子安怀恩成了四皇兄盛瑜的伴读。他总爱逗我,
或是突然从回廊转角跳出来吓唬我,或是故意抢走我手里的糖糕。每当我气得跺脚,
他便捂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四皇兄这时就会轻轻揉我的发顶,
笑着说:我们阿荣生气的样子也真可爱。明明听惯了溢美之词,可每当皇兄这样夸我时,
脸颊还是会发烫。如今我十六岁了,才明白那段时光是何等珍贵。那时的盛荣公主,
只需要烦恼今日的课业难得要命,御花园的蝴蝶为何不肯停在指尖。及笄后,
宫里的气氛日渐凝重。直到北国传来消息——他们竟将皇姐祭了战旗。父皇震怒,
潇妃娘娘一病不起。那晚我蜷缩在锦被里,忽然想起六岁那年随母妃去探望潇妃娘娘的情景。
娘娘一见我就落了泪,我笨拙地安慰:等阿荣长大了,一定把皇姐接回来。
可这句话不知为何,让满屋子的人都红了眼眶。皇姐那么好的人,待宫人宽厚,待弟妹温柔,
为何偏偏……我望着帐顶的流苏,眼泪浸湿了绣枕。这世间如此矛盾,
既有御花园的灼灼桃花,也有边关的累累白骨;既有母妃温暖的怀抱,也有北国刺骨的风雪。
翌日,四皇兄告诉我,安怀恩自请随父出征。我怔在原地,
突然想起前些日子他莫名其妙的问题:宴清,若有一天你再也见不到我,
会不会……有一点点想我?当时我还未来得及回答,他就笑着岔开了话题。现在想来,
原来他早就在道别。近来我常常望着宫墙发呆。母妃总说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
幼时觉得羞赧,如今却觉得,人生在世,能有些许放空自己的时刻,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只是每当回神时,
发现掌心攥着安怀恩去年塞给我的那枚铜钱——上面还残留着被我们刻得歪歪扭扭的平安
二字。最近我发现自己发呆愣神的时间变得更久了,母妃总说我从小便爱发呆,
从前总觉着丢脸想改过来,大了,又觉得人就活这么久,也不能想怎么样便怎么样,
这种想做又可以做的事这么少,便该珍惜着。北国为此次战争准备了许久,兵强马壮,
尽管安将军骁勇善战也隐隐有压不住的趋势了。这种情况下,结局究竟会是怎样呢。
收到宫人的传唤我踏进御书房,看见丞相、国师和皇兄们都在一旁站着,
只是皇兄们尤其是四皇兄的脸色并不是很好看,我便知晓了,
此次应该便是决定我的命运之事了。北境的战报一日比一日紧急。
安将军的军报上还沾着血渍,字迹却依旧力透纸背:"臣等誓死守关,
然敌军三十万铁骑来势汹汹..."我抚过那晕开的墨痕,
恍惚看见安怀恩执笔时颤抖的手腕。御书房的熏香太浓了,呛得人眼睛发涩。
我跪在冰凉的金砖上,听着国师亢奋的声音在梁柱间回荡:"七日后乃天时地利,
若以神女血脉祭天,必能...""荒谬!"四皇兄的佩玉撞在案几上,碎成两半。
他向来最重礼数,此刻却连冠冕歪了都顾不上,"父皇,北国狼子野心,
岂是...""够了。"父皇的指尖在龙纹扶手上敲出沉闷的声响。他看向我时,
眼底有我看不懂的浑浊,"宴清,你自幼受万民供奉。"我忽然想起及笄那日,
父皇亲手为我戴上的明珠步摇。当时他说:朕的盛荣,应该享尽世间荣华。
原来所谓的荣华,是要用血肉来偿的。"儿臣明白。"我伏身叩首时,
发间金钗在地面划出细痕,"愿为大盛赴汤蹈火。"四皇兄被侍卫带出去时,
月色长袍的广袖勾住了门环。裂帛声里,我听见他嘶喊中隐晦的提醒:"阿荣!
不要忘记皇兄。父皇赏了我七日清净。栖梧宫的海棠一夜凋零,母妃连夜送来的食盒底层,
藏着她当年入宫时的匕首。母妃一生温婉守礼,如今为了我,竟然默许了我内心深处的妄想。
我摩挲着刀柄上宁为玉碎的刻字,忽然想起那个上元夜——九岁那年上元夜,
我永远记得那场出逃。四皇兄和安怀恩一左一右牵着我的手,穿过宫墙的狗洞时,
我的裙裾沾满了泥土。长街上万千花灯如星河倾泻,我挣脱他们的手奔向糖人摊子,
再回头却已不见熟悉的身影。迷路的恐慌中,我听见巷弄深处传来幼猫般的呜咽。
拨开枯草堆,两个瘦小的身影正蜷缩在月光照不到的阴影里。
年长些的女孩用身体护着怀中的幼童,破损的衣领处露出狰狞的鞭痕。当她抬头时,
那双眼睛让我浑身战栗——像极了御兽园里濒死的幼狼。"拿着这个去余香阁。
"我解下腰间玉牌时,手指在微微发抖。女孩没有接,
反而警惕地将妹妹护得更紧:"贵人为何要救我们?"她嗓音沙哑,
每个字都带着刀刃般的戒备。这个问题让我如鲠在喉。难道要说,
是因为你们让我看见了自己锦衣玉食的罪恶?最终我只能落荒而逃,连名字都不敢留下。
那夜之后,御膳房精致的点心总让我想起女孩嶙峋的肋骨,
四皇兄说我突然像长大了十岁一般。而今夜,祭坛前的梨汤氤氲着熟悉的味道。
小太监摘下帽子的瞬间,我认出她正是当年那个女孩——如今她眼角有了泪,
眼神却比当年更亮。"盛荣大人,"她这样唤我,"您救过的每个孩子,都愿意为您赴死。
"我望着窗棂外皎洁的月亮。原来命运早在那年上元夜就埋下伏笔,我们这些困兽,
终究要撕开这吃人的尘世。我坐到马车中,喉咙里还残留着梨汤的甜腻。身下摇晃的马车,
帘外传来市井的喧闹——叫卖声、马蹄声、孩童的嬉笑,这些曾经离我很远的声音,
此刻却无比清晰。我挣扎着撑起身子,身上华贵的宫装已被换成粗布衣衫,
发间珠钗尽数卸去,只余一根木簪松松挽着发。"殿下?"车帘被掀开,
一张熟悉的脸探了进来。是我在余香阁中的女侍——她如今作妇人打扮,却添了几分沉稳。
她端来一碗清水,现在我们已经离皇城三百里,很快就能到北境。我接过碗,
指尖相触时感受到她掌心的厚茧。阿荆,你当年为什么取名叫这个。
"奴婢当年没有名字。"她垂眸,"当年您救下我后,余香阁的嬷嬷叫我阿荆,
说是野草命硬。"马车忽然颠簸,水洒在我手背上,凉得刺骨。阿荆急忙用袖子替我擦拭,
我却盯着她腕间露出的刺青——那是一朵小小的荣花。"这些年..."我的声音有些哑,
"你们一直在暗中,受苦了"阿荆笑了:有殿下这话,奴婢一点也不觉得苦。
她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封皮上赫然盖着四皇兄的私印。"殿下这些年暗中收留的孤儿,
都在北境等着您。"她翻开册子,密密麻麻的名字如蚁群般排列,"我们建的学堂、药坊,
还有..."她突然噤声。马车外传来整齐的马蹄声,接着是兵甲碰撞的脆响。
阿荆瞬间绷紧身体,一只手按在了座位下的短刀上。"例行搜查!"粗犷的男声逼近,
"车里什么人?"阿荆从容地掀开车帘:官爷恕罪,我家小姐是将军好友,
正要与将军叙旧。透过缝隙,我看见骑兵铁甲上沾着新鲜的血迹。
他们胸前的徽记是安家的家纹。为首的军官不动声色地同阿荆交换印记,
就在他要向我这边车帘行礼时,远处突然响起号角声。报——!北境敌军暴动,
将军令全军即刻回防!不必虚礼,快去吧。我出声道。谢殿下。
他带着骑兵们匆匆离去,扬起漫天尘土。阿荆放下车帘,
从座位暗格取出一套粗布衣裳:请殿下更衣,我们改走水路好避开交战。我接过衣服时,
摸到内衬绣着的荣花纹样。这针脚我很熟悉——是母妃最拿手的双面绣。马车转向东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