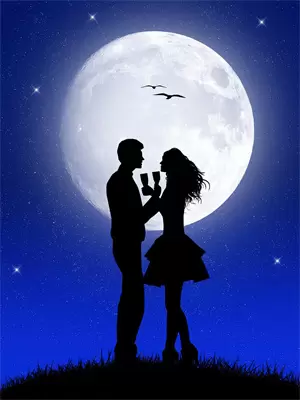姐姐把全家福发到朋友圈时,我正在啃苹果。“妈,你看李悦评论了!”她突然咯咯笑起来,
“她说小默不是咱家亲生的吧?”我的心猛地一沉。妈妈接过手机,笑容僵在脸上。
她沉默太久,久到空气都凝固了。“这孩子,真会开玩笑。”妈妈把手机塞回给姐姐,
声音有点干,“别理她。”可她的手在抖。我第一次发现,妈妈不敢看我的眼睛。
那句玩笑像根刺,扎进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里。第一章:定格的阴影我是家里最丑的小孩。
这个认知,不是某个瞬间突然领悟的,而是在漫长岁月里,
从亲人欲言又止的眼神、亲戚们心照不宣的调侃、甚至陌生人无意间的对比中,
一点一滴渗入骨髓的。我叫林默,这个名字取得恰如其分。在这个四口之家里,
沉默是我最安全的保护色。而我的姐姐林薇,比我大两岁,
在就像是为了印证造物主的偏心 -她完美复刻了母亲沈桂芬所有的优点:白皙透亮的肌肤,
水汪汪的杏眼,挺翘的鼻梁,笑起来时唇角两个浅浅的梨涡甜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而我呢?
邻居张阿姨有一次酒后吐真言:"小默这孩子,长得...挺有特色的。
"她说这话时眼神飘忽,语气里的勉强连十岁的我都听得出来。我们并肩而立时,
不像是血脉相连的姐妹,倒像是精心编排的对比图 -她是被上帝亲吻过的杰作,
我是造物主随手甩出的泥点。微黄的皮肤,单眼皮,鼻梁有些塌,嘴唇也略显丰厚。
每次家庭聚会,我们俩都是亲戚们目光的焦点。"薇薇真是越来越像你了,桂芬。
"大姑总是这样开场,手指轻轻拂过姐姐顺滑的黑发,"这大眼睛,这皮肤,真会长!
"然后,那些赞叹的目光会像探照灯一样扫到我身上,气氛会有那么一瞬间的凝滞,
接着便是更微妙的找补:"小默嘛...嗯,长得挺...大气的,有福相。
"福气 - 这个世界给不好看的孩子最体面也最敷衍的安慰奖。母亲通常会尴尬地笑笑,
下意识地把我往身后拢一拢,说一句:"我们小默学习好,懂事。
"父亲则会沉默地拍拍我的头,他的手掌温暖却短暂。这种无处不在的比较,像南方的梅雨,
无声无息却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姐姐穿剩下的、依旧漂亮的裙子,
到了我身上总显得哪里不对;每年的全家福,
我永远是边上那个需要摄影师反复提醒"笑一笑"的僵硬存在;就连过年拿红包,
亲戚给姐姐时是"买花戴",给我时则是"多买点书看"。十三岁那年,
意中听到母亲和姨妈聊天:"要是小默有薇薇一半漂亮就好了..."那句话像根细小的刺,
扎进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多年后依然隐隐作痛。
我渐渐习惯了活在姐姐耀眼的光环投下的阴影里,甚至开始主动将自己缩进阴影的更深处。
我放弃了和姐姐争抢漂亮发卡,默许母亲把我的照片收进相册最里层,
在别人夸赞姐姐时自觉地后退半步。我以为这样,就能安全一点。
第二章:朋友圈的利刺那是一个寻常的周六晚上,刚结束家庭聚餐,
空气里还飘着红烧肉的余香。姐姐林薇心情很好地窝在沙发里,
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快地滑动,挑选着今天拍的照片发朋友圈。"妈,你看这张怎么样?
"她把手机递到母亲面前,屏幕上是我们四口的全家福。照片里,父母坐在前面的藤椅上,
笑容温和。姐姐亲昵地搂着妈妈的肩膀站在后方,她穿了件新买的碎花连衣裙,明艳动人,
像是刚从时尚杂志走出来的模特。我站在最边缘,穿着简单的白T恤和牛仔裤,
努力想扯出一个自然的笑容,嘴角却僵硬地向上翘着,眼神里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局促。
"挺好的,薇薇真上相。"母亲笑着点头,眼角泛起细密的纹路。姐姐满意地收回手机,
指尖轻点,九宫格瞬间生成。滤镜很美,暖黄色的调子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温馨和谐。
我习惯性地点开朋友圈,准备点赞。手指悬在屏幕上方的那一刻,
一条新跳出的评论刺入眼帘。是姐姐的高中同学李悦,一个很活泼的女生,我也见过几次。
她评论道:薇薇全家颜值都好高啊!你妹不是亲生的吧?哈哈!
下面立刻有人跟评:就是,怎么跟你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呢?"嗡"的一声,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手机屏幕的光,此刻像手术台上的无影灯,将那些文字照得无比清晰,
也无比残酷。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褪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手脚冰凉的麻木。
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话了。七岁那年,邻居家的奶奶拉着我和姐姐的手,端详了半天,
最后对母亲说:"薇薇像你,小默...像她爸爸?"母亲当时的笑容有些勉强。
十岁家庭聚会,一个远房表哥喝多了,大着舌头说:"这两个姑娘真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
差别也太大..."可当它以文字的形式,如此赤裸地呈现在公开的网络空间,
呈现在我和姐姐共同的朋友圈里时,那杀伤力是呈几何倍数增长的。
它不再是可以假装没听见的窃窃私语,而是白纸黑字的"证据"。它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
精准地捅穿了我用十几年时间勉强筑起的、脆弱不堪的自尊心。我死死盯着屏幕,
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几乎握不住手机。姐姐回复了,她发了一个"笑哭"的表情,
加上一句:别瞎说偷笑没有否认。没有哪怕一句,
"我妹妹也很可爱"或者"不许这么说我妹妹"的维护。那个偷笑的表情像一根针,
细细密密地扎在我的心上。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浸入了冰水里,收缩着,疼痛着。
原来在姐姐心里,这也只是一个可以一笑而过的"玩笑"。母亲正好端着果盘走过来,
看到我脸色不对,凑过来看了一眼。她的笑容凝固在脸上,嘴角的弧度慢慢拉平,随即,
那熟悉的、带着复杂情绪的叹息,轻轻响起。她放下果盘,温热的手掌落在我的头顶,
揉了揉,什么也没说。可那无声的叹息和温柔的抚摸,比任何责骂都让我难受。
它仿佛在说:"看,我们都知道,只是没办法。"第三章:深夜的寻觅与尘封的铁盒那一夜,
我失眠了。窗外月色很好,银白的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上划出一道冷冷的痕。
朋友圈的评论像循环播放的幻灯片,在我脑海里反复闪现。
"不是亲生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些词语疯狂地啃噬着我。
委屈、愤怒、不甘,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自卑,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几乎让我窒息。
为什么?凭什么?就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就要承受这样的质疑和伤害?凌晨两点,
我鬼使神差地溜下床,像个小偷一样,蹑手蹑脚地走进了父母的卧室。他们睡得正沉,
父亲轻微的鼾声规律地起伏着。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
我的目光锁定了墙角那个老旧的胡桃木衣柜。我记得,家里所有的老相册,
都放在衣柜最下面的那个抽屉里。我像一个寻找宝藏的探险者,
又像一个试图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溺水者。
我想找到证据 - 找到我婴儿时期或许也曾可爱过的证据,
找到我和父母哪怕一丝相似的证据,来反驳那句恶毒的"不是亲生的"。
我小心翼翼地拉开抽屉,里面是叠放整齐的旧衣物,散发着樟脑丸和时光混合的味道。
我摸索着,相册没找到,手指却触碰到了一个硬硬的、冰凉的东西。
那是一个深棕色的、样式古朴的铁盒子,被压在几件厚厚的毛衣下面。它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边角甚至有了些许锈迹,锁扣的位置空着,似乎原本是有锁的。这不是放相册的盒子。
一种莫名的直觉,让我的心跳骤然加速。我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无法抑制那股强大的好奇心。我轻轻地将铁盒抱了出来,
冰凉的触感让我打了个寒颤。退回到自己的房间,反锁了门,我才感觉稍微安全了些。
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暖黄的光线照亮了这个神秘的铁盒。它没有上锁,只是卡得很紧。
我深吸一口气,用力掀开了盒盖。一股陈旧的纸张和墨水气味扑面而来。里面没有照片。
最上面,是一沓厚厚的、颜色不一的汇款单存根,用橡皮筋整齐地捆着。我拿起最上面一张,
纸质脆弱,仿佛一用力就会碎裂。收款人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 "王兰芳",
地址是某个遥远的、我从未去过的西北小城。再看日期,是从我三岁那年开始的,
几乎每隔两三个月就有一张,金额从最初的几百,到最近几年的上千,最近的一张,
就在半年前。汇款人,是妈妈沈桂芬的名字。为什么妈妈要持续十几年,
给一个远在西北的陌生人汇款?这个王兰芳是谁?我压下心头的疑惑,继续往下翻。
汇款单下面,是一张折叠着的、已经泛黄发脆的信纸。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展开,
生怕一不小心就把它弄破了。信纸上的字迹娟秀,却带着一种力透纸背的恳切与...哀伤。